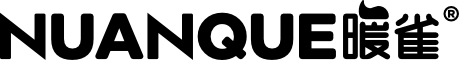◎发送信息
9月16日,贵州京剧院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在清华大学上演。 演出结束后京剧和ip形象结合的意义,有观众向我讲述了他们的观演感受:总体来说很爽,一会儿看电视剧,一会儿看模特表演,一会儿看杂技。 确实,这部演出融合了话剧的舞台管理、台词设计,以及舞剧、音乐剧等多个艺术门类的元素。
一方面,这部剧的主题——一个思想家(王阳明)的思维过程(启蒙)确实不具有戏剧性,所以导演需要丰富形式,让它不那么无聊; 但另一方面,这似乎是当代戏剧新剧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堪称“党心态”。
只有“情”、“物”、“理”齐全,才能获得真实感
中国以思想家为主角的戏剧数量较少,而以思想家思想过程为主题的戏剧则更少。 也许戏剧还是有一些表达这种思维过程的手段的,因为语言是戏剧的核心元素,而在后现代戏剧作品中,几乎不需要叙事,完全可以通过台词来体现哲学。
然而,歌剧作品要表达这种主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王国维谈戏曲“用歌舞讲故事”。 这个“载歌载舞”与音乐剧中的“载歌载舞”或者杂技中的杂技有很大不同。 它不仅仅是大规模拼接的一种形式。 “歌舞”在歌剧的结构中承担着特定的功能,营造了一种“情感氛围”。 音乐、歌唱、动作的设计实际上是为这种“情感氛围”服务的,而歌剧正是利用这种“情感氛围”来推进叙事、讲故事。 “情”有“物”作为支撑,所以是“物”中的“情”; “物”有“情”为线索,故为“情”中的“物”。 而“情”与“物”统一于戏剧的“理”之中:只有符合“情”与“理”的戏剧才能体现或反映某种“理”。 这个“原理”可以是哲学的,但绝不是“哲学的”,即纯粹抽象的。
在《阳明悟》的介绍中,特别提到本剧采用戏剧的“体验派”表演方式。 “体验派”作为一种培养演员的方法,在戏曲表演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新中国成立后,戏剧演员向戏曲演员学习。 比较重要的作品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制作的《蔡文姬》,当然还有《茶馆》。 后来,在“戏曲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弘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演出现代戏曲时,提倡戏曲演员深入生活、体验生活。 不过,后来不少戏曲演员对此提出批评。 比如,赵燕霞就曾以苏三为例来证明,完整的“体验”是不可能的。 此外,在苏联和西方戏剧界,通过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访苏,中国歌剧的表演方式也影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耶荷德。 训练方法也进行了一些修改。 例如,梅耶荷德提出“有机建模”。
《阳明悟》导演表示,在创作和排练中采用的所谓“体验派”方式,是针对传统京剧舞台上戏剧表演不完整的情况,即很多演员在表演时背过身去。不唱歌。 离开了戏剧性的情境,就连各路配角也都与剧情相当脱节。 本剧提到的“体验式”,就是让每个演员在舞台上时刻处于连贯的戏剧情绪,让整个舞台成为一个有机的表演空间。 这当然是真的。 转身走开、看似戏外的行为,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京剧的“角制”带来的,为了不抢对方的角色和风头。 在“娇儿制”诞生之前的戏曲中,比如昆剧,舞台的整体性和舞台上演员的配合度其实都很高。
可以说,舞台表演的完整性和戏剧故事的真实性才是使用“体验派”的目的。 但演员毕竟只是戏剧艺术的一部分。 演员能够参剧的前提是剧本逻辑自洽、情节合理。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身体设计和演唱安排符合节奏,才能充分调动演员的情绪。 只有“情”、“物”、“理”齐全,才能达到“体验派”所追求的真实性和真实性。 而这并不是戏剧的专利,真正的歌剧也有这样的追求。
如果剧本不存在,音乐怎么附上去?
虽然思想者的思维过程中涉及“情感”,但它毕竟是一个压抑“情感”的过程。 要冲破“情”的障碍,直见“道”。 因此,《阳明悟》的主题不仅不适合戏曲,甚至是“反戏曲”。 看得出来,主创煞费苦心地寻找故事,比如王阳明在京城的谗言,千里逃亡时的逃脱追捕,以及到达隆昌后与官员、苗民的交往等。 这些都是故事,适合用戏曲来表达,但这些“事”确实与王阳明的心理学思想关系不大,更适合讲述一个辞官归隐的故事,聚焦于山水,甚至讲述一个文化平等的故事。 ,主题是人人都可以成圣。
所以,当这些事情结束之后,突然引入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这几乎是全剧最尴尬的一段,也是观众和演员最累的一段。 这不是一个自然的进展,而是一个被迫的转变。 其实这部剧本来应该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最后却设计了一段师生对话的场面,引出了阳明心学最著名的三个故事:采竹、观花、刁翁。 这一幕的目的大概不是演戏,而是为了介绍这部剧的主题,让包括观众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化身为学生,走进阳明心学的“小课堂”,背道拜师。 。 总而言之,这是当场“圣化”王阳明的一段话。
这种戏剧设计在新剧中并不少见,与聚会套路十分相似。 有武术,有“歌”,有舞蹈,有对白小品,还有最后的主题升华。 整个表演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观众看得更轻松、更愉快,而不是讲述一个自洽、感人的故事。 每一段都可以明显看出导演的用意。 这一段用武术,下一段可以有抒情或说理的段,下一段可以用群舞,然后通过激情的旁白来烘托气氛。 在这样的处理下,歌剧真正被分解为形式元素,其技巧也真正成为程式化的技巧,甚至被观众称为“杂技”。
歌剧的程式化动作到底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日常生活动作的艺术表现,即美化真实的动作。 我认为这种理解并不准确。 在戏曲表演中,开关门、进出门、上下楼梯等动作在剧中的空间很小。 大多数动作与日常生活无关,而或多或少与心理活动有关——这些动作实际上是“情绪”的外在表现。 只有在情感和理性的支撑下,演员的思想已经到来,情感已经调动起来,才能通过这些动作与其他音乐语言的配合,最终打动观众。 没有逻辑的支撑和戏剧的完整性,技巧就无法服务于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推进。 毕竟,如果戏剧不存在,音乐又如何附着呢?
将历史视为“文化资源”之后
在此基础上,我们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该剧的介绍中专门提到该剧的文化与旅游融合非常成功,这确实是有意义的。 我们发现,近年来,各地戏班子上演了一批以当地名人(历史文化名人、当代榜样)为题材和主角的京剧作品:北京上演京剧《李大钊》、《石萍》等。昆剧《梅》、昆剧《曹雪芹》》,壮剧、习剧都编排了黄文秀的事迹。江苏省编排了昆剧《梅兰芳:梅兰》和《瞿秋白》,苏州编排了昆剧《千千》贵州除了话剧《顾炎武》之外,还以南仁东为基础编排了《阳明悟》、《天眼》……还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以说,在新历史剧的创作中,对待历史的方式有几种不同。 在传统京剧时代,过去的故事和事实是什么可能并不重要。 戏曲只是用这些故事来讲述一些古今相似的道理,也可能借古讽今表情包设计,如梅派的名剧《生死》、程派的名剧《阿闺梦》、《荒山泪》、著名齐剧《明末恩怨》等,这一时期的古今关系可以说是对联常有的。舞台左右两侧挂着“当代无往事,台下总有戏中人”。 新中国成立后,即戏曲改革时期,历史剧创作是在全面的历史观和历史框架下进行的。 戏曲故事被用来表达这种具体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观,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和结构分析就变得更加重要。
现在的新历史剧与前两种情况不同。 具体的历史情境、历史事实、历史观点并不是很重要,而且他们所讲的似乎也不一定是古今之间相同的真理(这样的剧有大量)。 该剧只讲述了当前的真相)。 唯一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历史上与创作者地理上有联系的名人——这似乎更像是IP化的历史书写。 这是一种“文化资源”的历史观,即文旅融合的视角。 历史文化服务区域发展,服务旅游品牌建设,用来提升区域在旅游市场的知名度。
这三种看待历史的方式不仅有各自时代的因素,也与艺术的资助方式密切相关。 这就是当前新剧创作的结构性条件,或许也是其困境的原因之一。
创建一个程序并不是“拿来”那么简单
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表演发展史上歌剧风格化动作的产生。 这些程序不是天生的、机械的、僵化的或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依赖于艺术家的创造。 在舞蹈方面,艺术家认为一部优秀的舞剧创造出一种新的舞蹈语言,可以丰富舞剧的表现力。 其实吉祥物设计,为什么新戏曲剧本作家不应该有这样的要求呢?
长期以来,戏曲多表现达官贵人、才子佳人,而很少描写底层人民和具体的劳动生产场景。 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改革过程中,艺术家们努力丰富戏曲表演的语汇,在服装和形体设计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经过他们的探索和积累,实现了革命样板戏的高潮,让歌剧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纯现代的生产生活场景,没有任何突兀感。
《阳明悟》中有一个场景,讲述了苗族长辈为王阳明盖房子的故事。 无论是动作还是场景安排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民族民间舞蹈是对本土原创舞蹈的艺术改进,戏曲也应该做出这样的努力和尝试,而不是仅仅“拿来”其他艺术形式的现成产品来直接使用。 其实,这一段如果能尝试用戏曲语言来表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特别是劳动活动,并发明一套新的风格化桥段,完全可以成为剧中非常丰富多彩的篇章。
贵州京剧院地处边疆地区,如何用戏曲语言表达少数民族的生活、生产场景应该是其主旋律。 这不仅会让一部作品更像一部歌剧京剧和ip形象结合的意义,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戏曲的表演形式,丰富了中国戏曲所能承载的意义和内容。
图片来源/贵州京剧院
- 本文固定链接: https://wen.nuanque.com/ip/21077.html
- 转载请注明: nuanquewen 于 吉祥物设计/卡通ip设计/卡通人物设计/卡通形象设计/表情包设计 发表
- 文章或作品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本文之内容为用户主动投稿和用户分享产生,如发现内容涉嫌抄袭侵权,请联系在线客服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本站转载之内容为资源共享、学习交流之目的,请勿使用于商业用途。